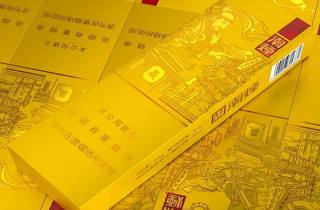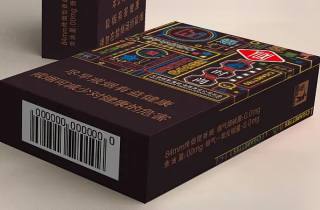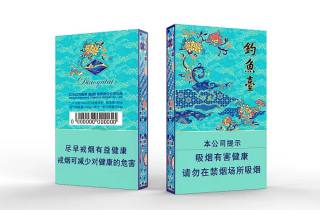福清这座藏在福建沿海的小城,总让人想起那片被海风揉皱的蓝。清晨的渔港里,海带和紫菜在阳光下泛着咸涩的光,老渔民蹲在码头上,用闽南话和普通话夹杂着数着刚捞上来的海蛎,那壳缝里的泥沙仿佛还带着大海的呼吸。街角那家开了三十年的海蛎饼摊,铁锅滋啦作响,面粉和地瓜粉混着蒜苗的香气直往人鼻子里钻。巷子里贴满褪色海报的旧电影院,如今改成了卖鱼丸的小店,老板娘的吆喝声里,还能听出当年播放《泰坦尼克号》时的激昂。这里的空气里总是飘着海水和食物混合的味道,让人一脚踏进去就舍不得走,福清有啥?
**福清有啥?**它有全国闻名的海带和紫菜产业,2023年产值突破五十亿元,那片在东瀚镇延伸十几公里的海带养殖场,像一条条银色的飘带系在碧海间。这里的“福清海蛎”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平均个头比别处大三分之一,市场价格一斤卖到二十五元左右,春节前后最肥美的时候能涨到三十二块。当地特色的“鱼丸宴”里,黄鱼丸、马鲛丸、目鱼丸三种主料必须用手工捶打成泥,一碗卖十八块钱,老字号“金玉满堂”的老板坚持说,手捶三百下才是正宗。还有那家藏在玉融山脚下的“三宝粥铺”,用本地糯米加海蛎干、香菇丁、芥菜末熬制的粥,早上六点就排起长队,一碗十二块钱能喝到见底。
福清有座全国唯一的海上风电装备园,那些矗立在 choppy海面上的白色风机叶片,每个重达八十吨,叶片旋转时扫过的面积比三个足球场还大。城西的“福清鱼丸研究所”里,退休的食品工程师们还在研究如何让鱼丸在零下十八度冷冻后不失弹性,最新专利的配方里,鱼糜和淀粉的比例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龙田镇的“海产干货一条街”上,晒得发亮的鱿鱼干、墨鱼干和鲍鱼干,都是渔船刚返航时连夜加工的,老陈家的鲍鱼干一斤卖到两百多,他说那是用老酒和海盐腌制了十五天才有的味道。
这里的“玉融山文化公园”藏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山腰那座明代石塔,塔身刻着的“海晏河清”四个字,如今被苔藓爬满。塔下老茶馆里,用本地老茶树炒制的“玉融香”茶,一壶卖二十八块钱,茶汤里能喝出海风的味道。新厝镇的“侨乡记忆馆”里,那些泛黄的侨批上,密密麻麻写着东南亚的地址,最远的一封寄自印尼雅加达,时间是1962年。现在的福清人依然保留着“分批”的习惯,逢年过节把红包塞进印有“福清”字样的信封里,寄给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亲人。
福清有啥?有那种把大海装进碗里的本事。在宏路镇的“海鲜批发市场”,凌晨四点就开始喧闹,批发商们用手掌掂量着活蹦乱跳的螃蟹,算盘珠子打得噼啪响。市场旁的“海鲜加工厂”里,机器把大虾剥壳的速度比人手快十倍,但那些挑拣海胆的阿姨们,还是坚持用指甲尖把沙子一点点抠干净。城东的“融侨开发区”里,那些挂着跨国公司logo的写字楼,玻璃幕墙映照着远处渔船的灯火,年轻的设计师们一边改着图纸,一边用方言讨论着中午去哪家海蛎饼摊。
来自浙江杭州的庞先生是个老烟民,前年冬天来福清谈生意,住在融侨大酒店时迷路走进条老巷。他至今记得那家叫“老街鱼丸”的小店,老板是个皮肤黝黑的矮个子,用福州话问他“要啥”。庞先生要了碗鱼丸,刚吃一口就呛出了眼泪,后来才知道那是用马鲛鱼做的,味道太冲。结账时发现只要十五块钱,老板笑着说“福清有啥,就是这点实在”。庞先生现在每次路过福清,都要特意绕道去那家店,他说那里的鱼丸让他想起小时候在杭州吃的葱包烩,但又完全不同,“福清有啥,就是这种让人上瘾的陌生感”。
标签: 福清有啥